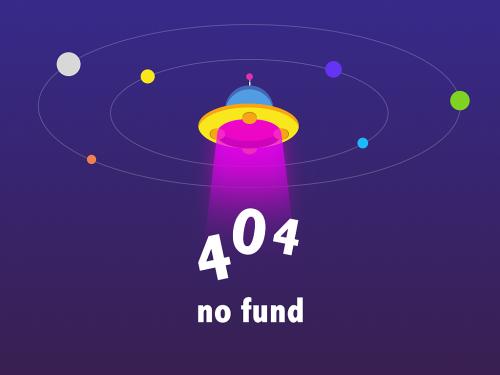短篇美文(精选5篇)-九游会j9备用网址
短篇美文范文第1篇
新时期文学,中篇小说曾经多么辉煌,而今天却仿佛到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长篇小说的书写俨然成为考量作家写作能力的试金石。
契诃夫、卡弗、博尔赫斯这些疏于长篇小说的大师,如果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势必也得灰头土脸。而能够写出《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优秀长篇小说的迟子建,对长篇小说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几年前,迟子建就批评过当今长篇小说“藏污纳垢”。她说:“短篇小说,很像这些被打捞上来时流着珠玉一样泪滴的‘泪鱼’,它们身子小小,可是它们来自广阔的水域,它们会给我带来‘福音’,我不知道未来的写作还能打捞上多少这样的泪鱼。因为不是所有的短篇都可以当‘泪鱼’一样珍藏着的。但我会准备一个大箩筐,耐心地守着一条河流,捕捉随时可能会出现的‘泪鱼’。”
我相信,和“藏污纳垢”的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也应像短篇小说这样,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泪鱼”。而且,如果说短篇小说从体制格局上还有着内在的自律,可以控制作家不至于滑行到长篇小说的领地,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疆界就相当暧昧不明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下文学中泛滥着所谓“小长篇”的因由。“小长篇”是文学向市场妥协的一个怪胎。它纵容着作家不再耐心地收拾中篇小说的手艺,把中篇小说抻巴抻巴就整出个“小长篇”。然而,迟子建这些年来却持续地经营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双重夹击不但没有窒息她的中篇小说的想像和蓬勃生气,反而使她能够从短篇小说中汲取简约,从长篇小说中吸纳丰沛,在文学的领地里扎稳了中篇小说的营盘,证明了中篇小说同样可以做出自己的声势和气象,抵达世界的辽阔和幽深。
况且,迟子建卫护的不仅是中篇小说的文体尊严,而且是生命的美丽与庄严。《岸上的美奴》题记说,“给温暖和爱意”。迟子建对一切美好、易逝的东西抱有伤怀之美的爱怜,但她的小说从来不回避“人之恶”,趋善向美却不隐恶遮丑。迟子建小说中的“人之恶”往往在迷离的梦幻和柔软的善良中浮现出来,尖锐地刺痛我们。而越是靠近,时易世变,“人之恶”也像一树一树的阴影一枝一叶地扩大。《白银那》中趁着鱼汛囤盐提价致使整个村子鱼腐败的小店主;《青草如歌的午后》中溺亡自己傻儿子的父亲;《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更是一个如人间地狱一样暗黑、冰凉的世界。
……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所有的人性之恶像怀揣着匕首的刺客随时割破世界的温情。
有对人世间如此的洞悉,迟子建完全可以种植出文学田地的“恶之花”,但迟子建却让“温暖和爱意”的光照亮人间。我们相互敌意、伤害,但我们又相濡以沫。这是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却支撑活着。作为一个作家,迟子建似乎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同样可以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就像她说的:“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却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事一回。”
有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强大的,但比起恶来,爱与美更强大”。我们读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从她的悲悯和宽宥之心看去,我们每个人原来都揣着良善之心,或者,只要我们愿意把那些自私、猜疑、嫉妒、贪婪、残忍从我们的心底赶走,世界将会重新接纳我们。
短篇美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欧・亨利 写作手法 布局 语言 结局
欧・亨利(1862-1910),原名william sydney porter,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曾被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欧・亨利的小说善于描写美国社会尤其是纽约百姓的大众生活,布局精妙,语言极具特色,以其独特的写作方法而享誉世界文坛。他一生写了270多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以“含泪的微笑”的风格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他的作品艺术特点突出,其中《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树叶》、《警察与赞美诗》、《带家具出租的房子》等作品,被誉为世界优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本文通过对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写作手法的详细分析,来探讨欧・亨利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所讲述的,是一个圣诞节里发生在社会下层的小家庭中荒唐却又感人的故事。男主人公吉姆是一位薪金仅够维持生活的小职员,女主人公德拉是一位贤惠善良的主妇。他们生活贫穷,但却各自拥有一样极其珍贵的宝物――吉姆有祖传的一块金表;德拉有一头美丽的瀑布般的秀发。为了能在圣诞节送给对方一件礼物,吉姆卖掉了他的金表为德拉买了一套“纯玳瑁做的,边上镶着珠宝”的梳子;德拉卖掉了自己的长发为吉姆买了一条白金表链。故事虽小但是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温暖、亲情、至爱、忠贞。在艰难困苦环境下一对相依相爱的夫妻,用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去换取对方所心爱的礼物。故事虽说是有些悲剧性的色彩,但是烘托出来的却是比万金更要贵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综观此篇小说,探究欧・亨利的写作手法,笔者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布局精心巧妙
欧・亨利的小说往往在开篇为故事的发展做精心的铺垫,各个部分联系紧密,故事的首尾形成一个自然不可分割的整体,使文章全部的故事情节合理。《麦琪的礼物》开篇写道:“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个、两个向杂货铺、菜贩和肉店老板那儿死乞白赖地硬扣下来的,……当时脸都臊红了……”这一段包含了整篇故事的全部要素。以“一块八毛七分钱,全在这儿了”这句开篇,说明主人公的贫穷程度,“其中六毛钱还是铜子儿凑起来的”,是“死乞白赖”得来的,说明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脸都臊红了”展示了主人公德拉善良的本性,寥寥数语就将人物完整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开篇的简洁与流畅,自然会使得文章的思路通顺。
此外在欧・亨利的小说中几乎每篇都可以看到两条线索同时存在,并且形成强烈的对比,以期实现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在《麦琪的礼物》文中,德拉卖发买表链是一条线索,而吉姆卖表买发梳则是另一条线索。整篇小说是通过两条线索的碰撞与交汇来梳理的,因而两条线索缺一不可。而这两条线索一交汇,作者就将整个故事结束。主人公生活的艰辛和窘迫、爱的真挚和深沉,都极好地体现在这一结构中。达到了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效果。因此两条线索并进,在欧・亨利的创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语言极具特色
作者在文中写的是一对穷困贫寒的年轻夫妇,圣诞之际互赠礼物,以此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无法避免的凄凉,不幸的生活遭遇。在描写他们的贫困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选词之精确和句式之灵活。在《麦琪的礼物》一文中,作者精心挑选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来刻画主人公的动作、外貌、内心以及生活情境。如在“rapidly she pulled down her hair and let it to its full length.”这句话中,动词pull down和副词rapidly均体现了德拉想为丈夫买一份圣诞礼物的急切心情。此外作者文中的句式也是相当灵活。有倒装句、长句、短句、断句、松散句、掉尾句等各式句型。如on went her old brown jacket;on went her old brown hat.(倒装);it was a platinum for chain simple and chaste in design,properly proclaiming its value by substance alone and not by meretricious ornamentation-as all good things should do.(长句);one dollar and eighty-seven cents.that was all.and sixty cents of it was in pennies...three times della counted it.one dollar and eighty-seven cents.and the next day would be christmas.(短句);only$1.87 to buy a present for jim.(断句);twenty dollars a week doesn’t go far.(松散句);three times della counted it.(掉尾句)。这样一些句式的使用使得作者的表达精确,有效地突出了作者的意图,塑造了一对贫困青年夫妻互敬互爱的艺术形象。
三、结局出人意料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常常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因此被誉为“尾巴的大师”。德拉卖了金发给丈夫买了表链,而且是跑遍了全城才买到的;吉姆卖了金表给妻子买了和金发相配的梳子。他们为了对方而各自失去了心爱之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然而作者采用这种构思,说到底也是为了造成强烈的悬念,从而形成一个令人惊愕、意外而又不违情理的精彩结局。这也形成了欧・亨利小说的独特风格。结局出人意料,而又合情合理。
参考文献:
[1]樊林.“欧・亨利式的结尾”表现手法浅析[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04期.
[2]李国宁.欧・亨利式结尾的艺术魅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文翠.从《麦琪的礼物》看欧・亨利的写作手法[j].东疆学刊,2001年,01期.
[4]刘新义.论《麦琪的礼物》语言特色[j].济南大学学报,1995年,02期.
[5]张经浩.欧・亨利短篇小说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短篇美文范文第3篇
周继松的《基准炮长》《弹道有痕》和《排长》(《文艺》第4期),显示了基层业余作者扎实而细腻的生活体验。醉心于操炮的炮手邱虎,在遇到人生中最大的抉择时,反而失去了操炮时的那种忘我境界,落入了世俗的旋涡;崔大炮心中对于大炮的那份真情,让我们看到了军人精神的传承;排长牛小宝看似在意提干,实质上是对于自身价值的诉求和张扬。王凯的《一日生活》(《西南军事文学》第1期)以连队一日生活内容结构全篇,充分显示了作者对连队生活的熟稔程度和在日常生活中品出滋味的能力。在和平年代军人常态化生活中开掘意味,寻找生活的意义和文学的价值,是军旅短篇小说的主攻方向。诸如李雷的《纯净时光》(《文艺》第1期)、李俊的《两个兵的非常时期》(《西南军事文学》第3期)、兰云峰的《月亮挂在天上》(《文艺》第9期)、王玉珏的《河东河西》(《文艺》第9期)、夏天的《舒服》(《神剑》第5期)、姚闻的《视线》(《橄榄绿》第1期)和袁常洲的《老兵》(《橄榄绿》第2期)等,这些作品立足于直线加方块生活中生成的军营文化,呈现独蕴意味的特质和形态,以军人自身完整的话语体系,叙述诸如军人的服从意识、强烈的不可抗拒的等级观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程式化生活、新老兵间守望与相融的关系等等。这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条件、不同政治环境里成长的青年,一旦参军到部队,就必须在军营文化的浸染下生活。从对故乡或社会文化的全部或部分断奶引发的文化休克,到主流上接受军营文化而又不时试图冲破,再到这种文化植入血脉无法舍弃,这是当兵的过程,更是生命一个又一个不可淡薄的状态。正是这样,同为军人的女兵也显得与众不同。夏凡的《我的亲密战友于小兰》(《西南军事文学》第4期)身上所散发的直率、阳刚,与其说是呈现男性化倾向,还不如说是她们悟化了军人所独有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作风;张慧敏的《心底的号角》(《西北军事文学》第1期)中耿岚因为家庭出身没能参军入伍,抱着非要当兵的念头跟到部队营区附近,以自己的方式执著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心中始终高响着走进军人行列的号角。这两位女性作者所写的女兵形象,表面上看似乎淡化了女性本身的柔美,但却将女性当有的坚韧与军营文化的个性达到了和谐,从一个侧面传达出文化的力量。
生成于上世纪80年代的浓郁“兵味”,是当下军旅文学还难以逾越的高度。然而,“兵味”不只是飘浮于作品的外在,弥漫于我们的阅读感觉,而是要让兵味与军人的成长形成观照。可以说,当下此类的军旅短篇小说,正是因为对军人特质的掘进不够,有“兵味”的气息,却无“兵味”当有的文化魅力;有鲜润的生活,却没有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作品难以上更高的层次,更为艺术化地铺陈军营文化和军人生活成长的心路历程。
2007年度的军旅短篇小说,在关注军人情感和回望战争两大主题上,显得有些单薄。原因一是指涉军人情感的创作,沾染上了经验化叙事的顽疾,突破的难度相当大;二是有着充分情感体验和历史学养的作家早已丢下短篇小说,在其他阵地拼杀;三是基层业余作者想像力缺乏,创作积累不够。值得一提的有王棵的《暗自芬芳》(《芒种》第6期)和裘山山的《事出有因》。《暗自芬芳》中的陈晴与王军那种朦胧清新的情感,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下闪现着瞬间的光芒,是诗意的、美好的,又是生活的某个细节。王棵力非写情,而是在寻找人性之中那种极其微妙、稍纵即逝却又营养生命的触点。作者从容的叙事把控和人物心理的刻画,是相当出色的。《事出有因》其实是一个有关现代军人与战争时代军人共同遭遇的叙事,裘山山的创作意旨进入的是关于人的处境的某种尴尬与无奈。真正的事实,当事人是最清楚的,但当事人却无法自我辩解,看似滔滔不绝,其实是处于失语状态。这两个短篇给我们一个提示,军旅文学的创作最终还是要在挖掘军人在军营文化浸染之下的精神处境和人性色彩。
短篇美文范文第4篇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情缘
徐志摩曾于1921和1922年留学英伦,其间他与英国名士多有交游,其中就包括当时业已成名的曼斯菲尔德。徐志摩以诗人出名,但在其文学生涯中,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同步进行。1923年1月9日,曼斯菲尔德不幸与世长辞。消息甫一传来,与曼斯菲尔德有过一面之缘的徐志摩就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诗作《哀曼殊斐儿》(解放之前,我国对katherinemansfield的译名不甚一致,有时译为曼殊斐儿,有时译为曼殊斐尔,现统译为曼斯菲尔德),由此拉开了在我国译介曼斯菲尔德的序幕。徐志摩对曼氏的文名极为仰慕,“除了哈代和泰戈尔,曼斯菲尔德是徐志摩有过短暂会面并留下愉快持久印象的第三位作家”(陈琳、张春柏:《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徐志摩一生译作数量虽然不在少数,但在《玛丽玛丽》的译序中他却写道:“除了曼殊斐尔说是我的溺爱,其它的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的会面,仅有20分钟时间而已,加上曼氏病体孱弱,二人意欲深入交流的效果必然打了一定折扣。不过细读悼文《曼殊斐儿》,徐志摩对曼斯菲尔德犹如教徒般的朝圣情感清晰可见。允诺徐志摩翻译其作品也许不过是曼斯菲尔德的说者无心,但徐志摩却用尽毕生精力践行了当时的承诺:“我承作者当面许可选译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应珍重实行我翻译的特权,虽则我颇怀疑我自己的胜任”。
从1923年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儿》至1931年飞机失事遇难,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徐志摩就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金丝雀》等10个短篇故事,翻译了《会面》、《深渊》和《在一起睡》三首诗歌,另撰有《哀曼殊斐儿》、《曼殊斐儿》、《评曼殊斐儿小说〈幸福〉小序》和《评曼殊斐儿诗三首前言》诗文4篇。1927年4月,“在1920—1930年代曾经引导一时出版风尚”的北新书局还推出了《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而其译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波澜
徐志摩不仅自己动手译介曼斯菲尔德,而且力劝好友陈西滢加入到翻译曼斯菲尔德的行列之中。陈西滢对英国文学文化了解颇深,谦称才力不足的徐志摩自然会力荐陈西滢为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出手相助。陈西滢后来果然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和《太阳与月亮》两个短篇故事,其妻凌淑华也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小姑娘》,凌淑华甚至因文风与曼氏的相似而被誉为“中国的曼斯菲尔德”。
徐志摩译介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文人作家。徐译曼斯菲尔德产生的效应犹如涟漪一般,一圈一圈荡漾开去。因为觉得徐志摩《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的译文不尽如人意,翻译家张友松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的方式,以幽默诙谐的方式指出了徐译的不足。徐志摩曾经表示,《英国曼殊斐尔小说集》“是他自己表示最可纪念的译品里面摘录出来的”。但在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张友松却指出了徐译中存在的多处不足:“他给曼殊斐尔修改的地方,在他译的那一个集子(约二百西页)里,当在三百处上下……此外还有些地方,诗哲干脆把原文删去一点,不过那也许是手民删去的,不一定能归功于诗哲……徐诗哲的译文与原著之不同,不消说,是修改,不是误译”。
虽然批评徐译不够精确,但张友松却不得不承认:“前几年他(指徐志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那篇‘曼殊斐尔’,不知多少人狂了似的捧着朗诵,有的人简直拿来背诵”。胡文则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为徐志摩的《曼殊斐儿》之动人效应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今日读了‘曼殊斐儿’一文,果然被他感动得最深,好似引我入了天国,把一切苦恼都忘去了”。阅读《曼殊斐儿》能让人想到人生中刹那的美感,胡文以为“这篇文字将曼殊斐儿叙述得声色俱佳,我们好像在梦里或生前,也在彭德街第十号楼上也受过了她底洗礼的”。徐志摩译介曼斯菲尔德产生的动人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短篇小说作家”曼斯菲尔德在中国
从整体来看,解放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主要强调其英国身份并且凸显其短篇小说创作。曼斯菲尔德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她的创作又不局限于短篇,而是涉及了短篇、中篇、诗歌、书信、日记、文学评论等诸多领域。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对曼斯菲尔德的翻译和介绍更加注重的是其短篇小说。
对于曼氏的短篇小说创作,国内的译介者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再说一次曼殊斐儿》将曼斯菲尔德称之为“天才”,声称短篇小说到了曼斯菲尔德手中“才是纯粹的美术”。小说集《曼殊斐儿》把曼斯菲尔德与格调不高的一般作家进行了区分,认为“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而曼氏“却只想留下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
对曼斯菲尔德这样的评价颇有些中国古代盛行的感悟式文学点评的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译介者用相对较为理性的话语对曼氏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郑或在看到曼斯菲尔德深受契科夫影响的同时,指出曼斯菲尔德“绝不会陷落陈套,反而是在走着一条崭新的艺术的路”。俞大薩将曼斯菲尔德置于整个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量,认为“在过去的欧西文学里,———尤其是在英国文学里,直到最近百年,短篇小说没有争取到一个显著的地位”。在20世纪之前,“英国文学里的短篇小说,好像流产的婴儿,面目模糊,根本不值一看”。如果说在曼斯菲尔德之前,“英国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未成形,懦弱,无自信的文学体裁”,那么曼氏的横空出世,则使得“英国的短篇小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独立的,前途无限文学表现”。曼斯菲尔德推出的几部短篇小说集,“将整个短篇小说的进展转上一个崭新的途径”。
翻译是文学接受的媒介,也是文学接受的一种形式。评介则是在广义的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更深一层的文学接受。无论翻译还是评介,它们都“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方梦之主编:《译学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81页)。从整体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虽然零星分散,且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它们却相对及时地把曼斯菲尔德的作品引入了中国,这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对曼斯菲尔德大规模的翻译、研究和接受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短篇美文范文第5篇
创作年表
1997年,《山花》杂志“三叶草”栏目发表短篇小说《站在屋顶上吹风》等。
1998年,在《收获》、《江南》、《天涯》等刊发表短篇小说《扫烟囟的男孩》、《地震之年》等一系列充满探索风格的短篇小说,引起期刊界关注。《站在屋顶上吹风》入选《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日文)第ii卷第8号通卷44号。
1999年,出版随笔集《我们居住的年代》(作家出版社),短篇小说《明朝故事》入选《小说选刊》第9期。中篇小说《坐拖拉机去远方》,获1997――1999年度浙江省作协优秀作品奖。
2000年,创作长篇小说《饥饿的饲育》(未刊稿)。获该年度“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称号。
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2001年,《十月》发表中篇小说《一个长跑冠军的一生》、短篇小说《三生花草》等。
2002年,《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红色少年》等。开始转入历史散文写作。
2003年,出版合集《六十年代气质》、《孤独的慰藉》等。
2004年,在《江南》杂志开设“历史碎影”专栏。《新月的余烬》入选《名家推荐最具阅读价值的人物传记・2004》。《向西,向西》入选2004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名家推荐最具阅读价值散文随笔・2004》。创作谈《叙事:世界不那么完美的一面镜子》刊《当代小说》2004年第11期。
2005年,继续“历史碎影”专栏写作。《痛》入选《2005中国散文年选》,《转塘一夜》入选《2005中国精短散文一百篇》。